今天上午翻閱手機,突然見到馮天瑜先生去世的噩耗,不勝震悼,不禁回憶起與先生交往的幾段往事。
馮天瑜先生1942年出生於湖北紅安,1964年畢業於武漢師範學院,即任教於武漢教師進修學院,1976年任武漢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79年後相繼在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和武漢大學任教,著述等身,他是上世紀80年代推動文化熱的先驅人物,也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文化史學者。
馮天瑜幼承庭訓,聰慧過人,文革中他曾發表一篇《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得到最高領袖的贊揚。1976年中共中央中發4號文件中有一段最高指示說:「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馮天瑜當年只有30多歲,一時曝得大名,坊間盛傳「小馮壓倒了老馮」。
我本與馮先生素無交集,只是因為後來他要為其父的收藏編輯一本書,才讓我與馮先生有了聯繫。
馮天瑜先生的父親馮永軒,早年入武昌師範大學,受名師黃侃指導,奠定了紮實的古文字學基礎,1924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期,又得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諸位大師的親炙。馮永軒先生不僅是一位著名的學者,而且他平時還熱衷收藏晚清及民國時期名人的書畫及墨寶,極為珍貴。馮永軒先生去世後,這批藏品即由他的幾個子女收藏。後來馮天瑜先生勸說馮天琪諸兄長,決定將其收藏的書畫墨寶編輯成書,交由湖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書名即為《近代名人墨迹》。
我自1990年起即擔任饒宗頤教授的學術助手,出版社出版此書之前,馮先生希望恭請饒公題耑書名。出版社不知通過甚麼方式輾轉找到了我,馮先生也專門給我來信說明情形,我便從中幫忙,竭力勸說饒公為此書題名。記得第一次書名題好後,出版社及馮先生覺得不是太理想,但又不好意思說。我又請饒公再寫一幅,這種事一般很難開口,但饒公並未在意,很快又重寫了一幅,得到出版社與馮先生的莫大喜悅,我能為該書的出版盡一分力,也感到非常高興。
《近代名人墨迹》出版後馮先生即寄贈兩部到中文大學,一部饋贈饒公,以答謝他的關愛,另一部則送給我留念。我細心翻閱此書,發現內中收有屠寄先生的一幅對聯,因為屠寄是我太太表姐表哥們的曾祖父,我就將此幅對聯拍下照片寄給他們。屠家的後人均未見過先祖的遺物,突見此墨寶,非常高興,曾委託我與馮先生聯繫,詢問這幅對聯的來歷,並試探能否出資轉讓。因此我便與馮先生通過一次電話。馮先生說,他不清楚父親是如何得到這幅對聯的,而且明確回答父親的藏品不可能轉讓,但他可以饋贈一部畫冊給屠家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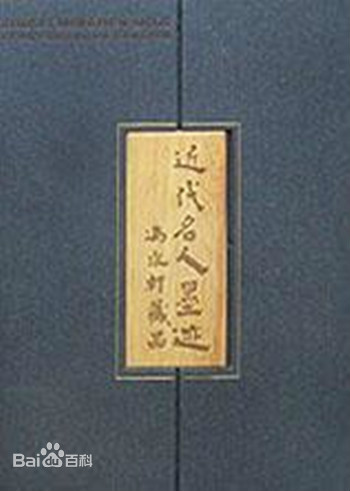
2005年,廈門的一位王維生先生找到我,說他們已與廈門大學文學院合作,並得到福建省和廈門市各級領導的支持,準備在廈門市的國家重點公園白鷺洲公園東邊篔簹湖側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書院,名字就定為篔簹書院。篔簹為竹之雅稱,書院建於竹林環水、桃李繽紛的市中心,其宗旨就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王維生來信稱籌備處盛情邀請饒公擔任書院的名譽院長,並懇請饒公為書院題名,對此饒公均欣然應允。其後我曾陪同維生兄親自到香港跑馬地饒公家中拜訪饒公,並恭送騁書,隨後還陪同王先生到香港大學參觀了成立不久的饒宗頤學術館。
2009年11月底,廈門的篔簹書院正式成立,並以此機會召開第一屆海峽兩岸國學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眾多著名學者參會。維生兄亦致函邀請饒公和我一同與會,但饒公因年邁不易遠行,便命我一人前去,並代表他向書院的成立表示祝賀。到了廈門,我才發現馮天瑜先生也應邀參加這次盛會,我雖然以前曾與他通過書信及電話,但見面這還是第一次,先生謙遜儒雅,深具大家風度。數天會上會下交流,我與馮先生多次交談,分外熱情。我將剛出版的拙著《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呈贈先生,他亦饋贈大著《「封建」考論》予我。上世紀90年代初我剛到香港,在不少學術會議上都曾親眼所見兩岸學者為封建主義這一名詞的定義爭論得不可開交,我雖然並不贊同所謂「秦漢之後皆封建」這一論斷,但卻不知如何分析和判定。今見馮先生的論著,真可謂醍醐灌頂,頓有耳目一新之感覺。馮先生不僅學問深博,而且還擅畫畫,他的速描可謂一絕,這也是我在會議中才得知的。一天會後,他突然交給我一頁紙,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我開會發言時他為我畫的一幅速寫,真是意外的驚喜。

2009年11月,在廈門與馮天瑜先生第一次見面。

2011年10月,香港有關單位邀請武漢市政府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聯合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的大會,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武漢方面章開沅、馮天瑜、馬敏等著名學者蒞臨報告,我亦有幸作為香港學者被邀請出席,並與他們同台報告。記得我報告的題目是《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報告結束後,得到章先生和馮先生的贊譽,這是我與馮先生的第二次相聚,雖然時間很短,但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6年我應武漢華中師範大學馬敏、朱英諸兄的邀請,到該校進行短期訪問,我原本計劃趁此機會再次拜訪天瑜先生。我曾託武漢大學的朋友聯絡,但聽說先生當時正在醫院休養,不方便見面,後來才得知他正在與癌症抗爭,然而我卻錯失了一次當面聆教請益的機會。在這之後我一直沒有機會與先生見面,直到前兩年有個朋友將我拉入一個微信群,赫然見到先生亦在群內,即冒昧向他問安。馮先生亦非常高興,很快我們就私下建立聯繫。雖然暫時無法見面,但無往弗屆的網絡將我們聯繫在一起,我經常看到他發表的文章,我也不時將一些消息和電子書傳給他,並將個人的新作送呈請教。我說起前次去漢時無法相見的遺憾,他即說沒關係,等到疫情結束後歡迎再次訪問武漢,重敘友情。
去年11月世界杯開鑼,馮先生每天都在微信中發布他對比賽的預測,他的預判基本上都正確。12月4日他在發給我的微信中說:「我把球賽預測作為一種思維體操。要領:(一)據之以實情、實勢的把握(故必須掌握真實的而不是虛構的過往事實);(二)以理性思辨判之,這裡須排除個人好惡、利益驅動的干擾;(三)信從必然性,又重視偶然性,必然寓於偶然之中,因而不迷信強者一定勝弱者,但強弱之勢必竟是判斷的重要依據,然又勿迷信於此,不堅執於通識性的強弱對比,有些事物隱忍未發,有外弱而內強者,有外強中乾者,這要求我們磨練由表及裡的透視力。總之,預測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需要重申----切勿自以為神機妙算,凡胎肉眼,哪裡能『神測』。」他接著又說:「有朋友要我預測時勢發展。大局走向,那已超出『游於藝』的測球範圍。淺見是有的,自信有三兩分道理,卻因沒有把握而又會觸忌,故不便細說,放在肚子裡發酵吧。」我為他的預測結果深感佩服,更為他的精密思維擊節贊嘆。
12月底突然在一個群中得知馮先生病重急需輸血,緊接著在朋友圈中有多位朋友發出呼籲,尋求血源,大家都在為他的病情而焦急奔走。不久又收到消息,說血源已經解決,馮先生業已轉危為安,正在為他能挺過這一關而感到萬幸之際,今天上午還是接到噩耗,說上午九時許還沒事,人也很清醒,但一個小時之後心贜就停止了跳動,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與先生雖然只有兩次相見,但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卻永遠留在心中。今日病失良師,謹敘數言,以寄託對先生的悼念與哀思。
書於2023年1月12日19:30